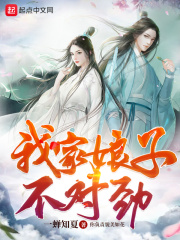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大明从边军开始覆明灭清92 > 第278章 崇祯九年发展规划二(第1页)
第278章 崇祯九年发展规划二(第1页)
交代完农部的工作后,江瀚将李兴怀送至殿门外,这才堪堪松了口气。
他躺在椅子上,一边闭目养神一边盘算着接下来的安排。
还没等他休息片刻,殿外的内侍便跑了进来,轻声通传道:
“大王,学部王承弼王主事已经在殿外候着了,您是要休息会儿还是。?”
“快请!”
江瀚精神一振,立刻从躺椅上爬了起来。
教育改革,也是他接下来要重点规划的方向。
见到王承弼这个老丈人,江瀚随口和他寒暄了两句,便直接进入了正题:
“王主事,学部明年的头等大事,就是要办一场覆盖全川的抡才大典。”
“眼下四川初定,各州县有不少空缺,急需补上。”
“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,就按上次保宁府的内容来。”
“往后,咱们的科举就不要再拘泥于四书五经,程朱理学了。”
“你王家是书香门第,应该比我更清楚其中利弊。”
这话像戳中了王承弼的痛处,他忍不住连连点头:
“大王所言极是。”
“大明科举自从太祖定下了八股取士的规矩,到后来是越走越偏。”
“几百年过去,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早就被翻烂了,圣人之言也被拆得七零八碎,不成样子。”
“不少士子为了中举,整天埋在故纸堆里,只知道皓首穷经;别说算学、农学这些实用的学问,就连基本的民生疾苦都不懂,实在是悲哀。”
江瀚点点头,沉声道:
“通过这种考试选出来的士子,很大部分都是长于空谈而短于实干的绣花枕头。”
“在我治下,这种酸儒一概不能为官,必须要是能理政的实干之才。”
可话虽如此,但改革绝非一簇而就的。
治大国如烹小鲜,最忌讳的就是急躁和一刀切。
江瀚担心的是,如今四川的大部分学子,自幼苦读的都是四书五经,如果骤然变更考试内容,只怕他们会无所适从。
王承弼对此也深以为然,点头附和道:
“大王所虑极是。”
“学子们寒窗苦读十余载,前半生所学皆在于此,如果骤然变易,恐生事端。”
“依臣下愚见,是不是可以把科举时间稍稍推迟,最好推迟到明年秋收之后。”
“同时,由我学部提前公布考试范围,除了传统经义外,增设算学、农桑等学科,并给出参考书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