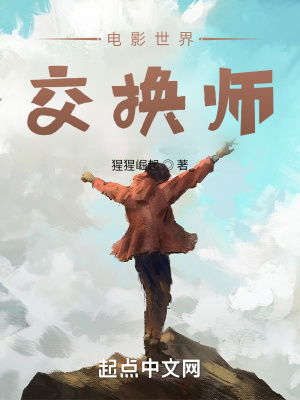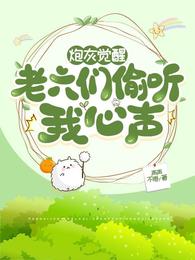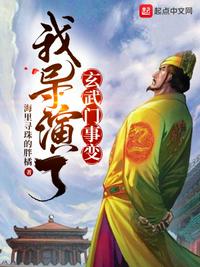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暖暖这二字是什么意思 > 第10章 闲时絮(第1页)
第10章 闲时絮(第1页)
林暖回到林宅时,江南的黄昏正慵懒地铺展开。
比起北地此刻或许早已沉入暮色,这里的天光依旧清亮,带着一种缠绵的暖意。
庭院里那几株去年移栽的石榴树,没能留住它初绽的许多花苞,橙红如霞的花瓣零落一地,在青砖地、花坛边、青草地上晕染开片片暖色。
她提着一只细竹编的篮子,弯着腰,小心地将那些尚且新鲜、未被踩踏过的落花一一拾起。指尖触碰柔软的花瓣,带着夏日余温的微尘气息,仿佛在拾掇那些散落在流年里的过往碎片。
她想着,过两日将这些花瓣洗净晾干,熬成一锅清甜温润的石榴花粥,好看又好吃,还养生。
一阵带着暑气的微风掠过庭院,卷起地上的微尘,也拂乱了林暖鬓边的几缕碎发。她下意识地抬起沾了些许花汁的手,将发丝轻轻别回耳后,露出光洁的侧脸。
就在这时,陈行宁下值归来,散去众人往后院而来,他一眼便望见了石榴树下那抹专注的、与落霞同色的身影,那瞬间的侧影在柔和的天光里显得格外温婉动人。
他快步走近,在她身旁站定,目光落在她低垂的眼睫和篮中渐满的落花上。
“阿暖,”他的声音放得很轻,带着归家后的松弛,自然而然地在她身边蹲下,“我帮你。”修长的手指也加入了捡拾的行列,动作轻柔。
林暖闻声侧过头,唇角漾开一个恬静的笑意,眼中映着黄昏的暖光:“没事,快捡完了。你看,这花落了也是可惜,能入食的……只是今年雨水太勤了些,又是头一年开花坐果,怕是难结出像样的石榴了。”她顿了顿,看着枝头零星的花苞,“回头得跟冯伯说一声,好好修剪下花枝,养一养,明年兴许就能盼到满园的石榴了。”
“嗯,”陈行宁应着,指尖捻起一片完整的花瓣,“阿暖爱吃石榴么?从前在家里,日子紧巴,好东西难得……这江南倒是四季鲜果不断,石榴也算寻常了。”
“一方水土一方人吧,”林暖直起身,将最后几朵花放入篮中,掂了掂分量,“江南湿暖,草木繁盛,日子……总归是比北地安稳些,也舒服些。”她话锋一转,目光落在陈行宁带着些许倦意却依旧清亮的眼睛上,“知远,你这些日子跑遍了越州各里各村,可有什么章程了?所见所感如何?”
陈行宁的眉头习惯性地微蹙起来,方才归家时的轻松被一丝凝重取代:“众生皆苦,这四个字,越走看得越真切。江南水土丰沛,谷物产丰,但压在百姓身上的担子也重。前些日子城西又有几个村子遭了水患,幸而这次水退得快,没酿成大灾,但被淹的房舍和泡坏的田苗,也够那些乡亲愁上许久。”他叹了口气,声音低沉。
林暖提着篮子站起来,关切地问:“你准备如何着手?”陈行宁也随之起身,两人并肩站在石榴树下,影子在暮色中被拉长。
“祝大人确实有远见,”陈行宁语气中带着敬佩,“当年在江口村修建的排洪口,如今看来是极明智的,这次水患能这么快控制住,它功不可没。
但隐患仍在,越州河在城西上游,若遇连绵大雨或上游洪峰,单靠排洪口怕是力有未逮。我思忖着,能否在城西上游寻一些合适的地界,修建一些水库。”
他目光望向远方,仿佛在勾勒蓝图,“越州不缺水,只是水太多太急,无从蓄积调停,有了水库,丰水时蓄洪,枯水时放水灌溉,方能缓解旱涝之忧。前几日我已让卢震带了几名懂些水利的老河工去勘察地形了。”
他顿了顿,又提起另一桩心事:“还有一事,这越州河穿城而过,东西往来竟无一座桥梁!百姓要去城西,要么绕行上游很远,要么只能搭乘小舟,既费时又不安全,汛期更是危险。我想着,若能建起几座桥……”
“建桥?”林暖立刻领会到其中的关键,“这可不是小事,需要精通水工、结构的大匠主持。江南……”她想起那些年的动荡,语气带着忧虑,“江南的能工巧匠,前些年折损得太厉害,或已罹难,或隐姓埋名不知所踪,这人才……恐怕是个大麻烦。”
“是啊,”陈行宁眉头锁得更紧,疲惫中透出几分无奈,“这正是眼下最棘手的一环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没有精于此道的匠师,图纸、工法都无从谈起。”
他揉了揉眉心,随即又带着一丝宽慰看向林暖,“不过阿暖你说得对,凡事急不得。比起初来时处处掣肘,如今局面已算好了许多。至少张、吴两家在明面上还算配合,肯给几分薄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