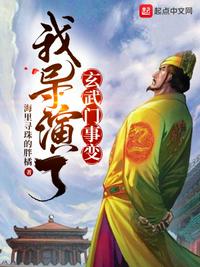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从魔都译制片厂开始 笔趣阁 > 第三百一十章 来自京城第一玩主的求助(第3页)
第三百一十章 来自京城第一玩主的求助(第3页)
“想起来了,”黄永钰可算是想起来了:
“那天我还没看清书名,就被你猛的抽了回去。当时我顺手就抄起桌上一個硬家伙,直接就想照你头上呼过去,后来一想是在光宇的屋,便又忍下了。”
当初王世襄倒不是看不起黄永钰,只因为此书晦涩难懂,一般人根本看不懂:“之后听了光宇的介绍,我才知道你是谁!”
又过了几天,黄永钰再去张光宇家做客时,屋里的王世襄直接站起身就冲了出去。
当时给黄永钰气的,说什么也要追出去干上一仗。
就在屋里的几位死命劝架的时候,王世襄又跑回来了。
双手递出一本书后,一字一句道:“我王世襄,你黄永钰,请欣赏。”
黄永钰低头^_^本,正是前几天的那本书。
好家伙,王世襄这招直接让两人化干戈为玉帛。
从此,二位大家便你来我往上了。
“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,还记着呢?”
黄永钰提着一把茶壶,为王世襄添了一杯热茶:“难道……你说的就是那本书?我记得那是一手抄本啊!”
“我可没那本事,”王世襄趁热喝了口茶:“三十年前,朱启钤老先生将这本交到了我手里,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好,遂将此书的诠释解说任务交予了我。”
说罢,王世襄将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并拿了出来。
一本是,另一本是的书稿。
看着书案上厚厚的书稿,黄永钰直接就愣住了:“你究竟为这书写了多少注解?”
“若论字数的话,”王世襄笑了:“这本注解已经是原书的20倍了,从1948年动笔开始,到1958年停笔,我整整写了10年……”
因为始终没办法出版,在之后的20年里,王世襄又不断的加以精雕细琢。
这才有了今日的规模。
看着眼前这位已快入古稀的老相识,黄永钰深深的叹了口气:“实不相瞒,我表叔那本书能得以出版,完全是托了我一位小友的福。”
“小友?”王世襄快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:“哪位小友啊,我怎么没听你提过?”
“你才回来多久啊,能听说就怪了,”说罢,黄永钰指了指桌上的牛皮纸包裹:
“我这位小友是浦江一报社的编辑,人缘好脑子活,改天我帮你问问这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