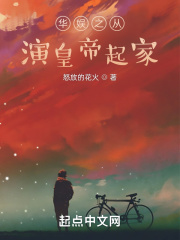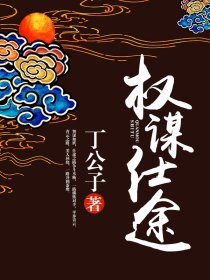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暖暖暖暖的 > 第37章 建桥(第2页)
第37章 建桥(第2页)
一位头发花白、面上带着风霜痕迹的老师傅忽然蹲下身,用手抹开地面上的一层薄土,露出底下略显异样的地基结构。他抬头望向楚师傅,语气中带着几分惊异:“老楚,你瞅,这儿是不是原本建过桥?这地面硬得不像话,土层底下像是埋过石基。”
林暖上前看了下,她感觉内心震颤了一下,感觉跟那石基像水泥路面破碎后的样子。
楚大人闻言也俯身细看,用手指叩击地面,又取出随身携带的探土钎向下钻探了几寸,眉头渐渐蹙起:“像又不像。若是旧桥基,历经这么多年水土冲刷,不该保留得这般完整。但这地势确实比别处平整,土质也紧密,倒是个天然的建桥好址。”他站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泥土,转向始终跟在身后的陈行宁:“陈大人,借一步说话。”
两人沿着河岸向南行出一段距离,直到其他工匠的交谈声渐渐模糊,楚大人才停下脚步,开门见山道:“陈大人,一般建桥无非石桥或风雨廊桥两种。石桥以巨石为材,施工难度大,耗时也长,但胜在坚固耐久,能历数百年风雨。不过石面遇雨雪易滑,行人需多加小心。风雨廊桥则以木材为主,上覆顶棚,雕梁画栋,既能遮阳避雨,又可成一方景致。但木结构需定期维护,且对木材要求极高,造价甚至可能超过石桥。”
陈行宁凝神听着,目光不自觉地投向对岸隐约可见的村落:“楚大人以为何种更适合越州?”
“此事关乎越州百姓长远福祉,本官自不敢独断。”
陈行宁微微欠身,“下官需与林氏、张家和吴家共同商议。此外,前些日子见卢大人,陛下似乎有意在长江试建桥梁,此次越州建桥亦可为将来积累经验。”
楚大人闻言露出赞许之色:“不错!我等从广陵坐船而来,深知长江天堑之险。越州河与长江相比,确实如溪流之于大江。但正因如此,越州之桥更须建得稳妥,既要便民,也要为日后大江建桥探路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道,眼中闪烁着工匠特有的热忱,“事在人为嘛。”
“楚大人所言极是,小子受教了!”陈行宁郑重行礼。
楚大人忽然话锋一转,语气中带上几分调侃:“不过这越州林氏那位小娘子倒是有趣得紧!听说你二人是夫妻,这般倾力为越州奔波,若是运气好,短则三年,长则六年,陈大人必得高升。何苦在此地耗费如许心血?”
陈行宁沉默片刻,目光掠过河面上零星穿梭的渔船,缓缓说道:“楚大人,在位一日便当尽责一天。下官的妻子虽为女儿身,却胸怀天下,常言‘为官一任,当造福一方’。下官愿与她同心协力,为越州百姓略尽绵薄之力,这也是下官的初心。”
楚大人闻言,肃然起敬,重重拍了拍陈行宁的肩膀:“是老夫狭隘了!你们尽快商定章程,材料筹备宜早不宜迟。”
“谨遵大人教诲!”
当日午后,陈行宁便在县衙召集了张家二爷(现越州张家话事人)、吴家家主及林暖共商建桥大计。
议事厅内,炭火噼啪,茶香袅袅,却掩不住讨论的热烈。
吴家家主首先发言,指节轻叩茶案:“风雨廊桥美则美矣,然造价高昂不说,日后维护更是无底洞,我等虽富庶,却也不必如此铺张。”他捋着胡须,目光扫过在场众人,“石桥坚固实用,百年不倒,方为上选。”
张家二爷点头附和:“吴家主所言极是。且石桥可与越州山水相映成趣,不必一味追求江南风雨廊桥的精致。实用为上。”
林暖想起前世在江南见过的那些古桥,有的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,木结构的廊桥不仅是一处交通枢纽,更成为一方人文景观,而且站在她的角度,似乎风雨廊桥与越州宴更配!
她便开口说道:“石桥固然坚固,但越州多雨,石面湿滑,老人孩童行于其上恐有风险,风雨廊桥虽造价稍高,却能遮阳避雨,成为百姓休憩之所,甚至可成越州一景。且木材若选用得当,工艺精湛,同样能够历久弥新。不过我倒也不是坚持,都可以!”
陈行宁静听各方意见,指尖无意识地在图纸上描画桥拱的弧度,最终,他综合考量各方因素,拍板定案:“既如此,第一座桥便定为石桥。但桥面可略作改良,凿防滑纹路,桥栏加高,以保行人安全。”
资金方面,最终议定由县衙、林氏、张家和吴家按照三、三、二、二的比例出资,并将在桥头立碑刻文,铭记四方功绩。
建桥方案既定,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采石备料。
越州多山,但并非所有山石都适宜建桥,城北的石灰矿表层石料尚可一用,但深层的石灰岩质地疏松,遇水易蚀,显然不合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