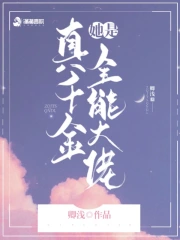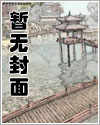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我的时代1979起点中文网 > 第四十九章 日常切片(第2页)
第四十九章 日常切片(第2页)
推开门,老式木桌后坐着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,桌上摊着一摞牛皮纸档案袋,搪瓷杯里的浓茶正冒着热气。
墙上贴着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的标语,被擦得干干净净。
“老师您好,我是许成军,从安徽凤阳来的。”
许成军把帆布包放在门边的木凳上,掏出省教育厅的介绍信和面试函递过去,“这是我的材料,朱教授让我这个月底来面试。”
教务员接过材料,抬眼打量他:“安徽的许成军?前一阵讨论你的事,系里好不热闹。”
他拿起钢笔在登记表上划了几笔,“《谷仓》那篇稿子,周明主编上个月还跟我们系主任通了电话。”
许成军心里一松,老周是真靠谱!
顺势从包里抽出《安徽文学》的用稿通知和《收获》的稿签:“这是近期发表和录用的作品,还有苏中和刘祖慈老师的推荐信。”
教务员接过材料仔细翻看,轻轻点了点头:“章培横教授特别交代,要看看你原稿的修改痕迹。年轻人能沉下心写农村题材,不容易。”
他把材料按顺序放进档案袋,用棉绳捆好,“校委会其实分歧不小。有人说知青学历浅,也有人说你的文字够格当‘特殊人才’。”
“理解。”
许成军笑了笑,“我在农村插队两年,知道教授们怕我理论底子薄。”
教务员诧异的看了他一眼,
这话看似谦虚,但是话里话外其实全是自信。
对自己的理论知识很自信?
这在知青里到是少见。
于是教务也有意无意的多叮嘱几句。
“但是从你的材料看,其实我认为是绝对够格,放在往年大可不用你来面试这一趟。”
“但是今年特殊,有消息说10月要全面取消工农兵推荐,本来在这风口上,复旦今年也是要停的,最后留了口子,但是全国也才十几个名额。”
“所以艰涩之处也请你理解。”
其实很多时候,你一句话就能改变别人的态度。
当然你也得知道该说什么话。
“当然能理解老师们的良苦用心,也让您和各位教授费心了。”许成军应道。
教务抬头看看许成军,笑了。
兴许是觉得这知青还挺有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