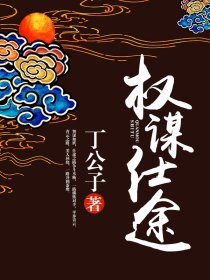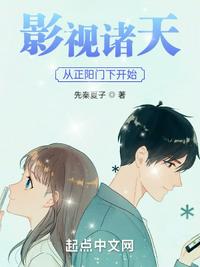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我的时代1979无错版 > 第七十一章 掌门亲传(第1页)
第七十一章 掌门亲传(第1页)
简单吃了几口,许成军又开始埋头苦写。
家乡是哪?
是那个永远回不去的2024。
但是这辈子许家屯是他的精神归宿。
是他未来一切的起点。
他写“野蔷生处是吾乡”,既是说这片田野成了他的根,也是说那些在苦难里挣生机的人们,让他读懂了“家”的真意。
阿秀摸过的蔷薇刺、夜里虫鸣织成的网……
这些温暖又扎人的细节,让他把异乡过成了故乡。
文字成了他与这片土地对话的方式,把眷恋、敬佩与期待,都种进了字里行间。
说到底,这篇文章是许成军的“心灵日记”,
他要用野蔷薇的荆条与新芽。
写下对土地的敬、对时代的悟,也写下一个写作者最本真的坚守。
好文字,从来都长在生活的土壤里。
苦难会留下痕迹,但希望永远比荆条更顽强。
生活或许满是荆棘,但总有新芽,从裂缝里挣向阳光。
良久,才从文字意向中抽离出情绪。
阿秀是谁?
柱子哥是谁?
是藏在77年之前的许家屯的旧事。
许成军揉了揉手腕,抬头看了眼挂钟,已经快要一点,抬头一看,门口的孙教务正提着个陶瓷缸子,右手拿了个布包。
“教授们,让我来看看你写的怎么样了,也拖我给你带了点吃的。”
“没吃饭饿坏了吧。”
孙教务笑着把杯子和布包放在了桌面上,态度明显更好了一层。
啊这,我是该饿还是不该饿呢。
算了,珍惜粮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