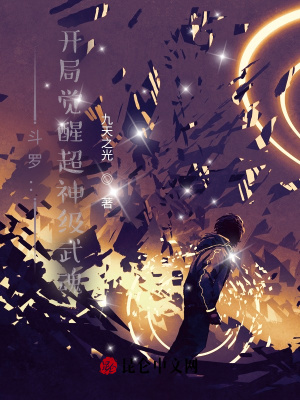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华娱从神棍到大娱乐家 篱笆好 > 第四百零二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向茜加更(第7页)
第四百零二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向茜加更(第7页)
她疯狂挥舞着双臂,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,却仍死死盯着那个“枪口”,浑身战栗如筛糠。
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,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,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。
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,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,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。
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,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,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。
“我。。。我叫夏淑琴。”
“中午有人敲门,爸爸去开门,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。。。”
镜头给到牧师约翰·马吉的手持摄影机,在他的镜头里,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。
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,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,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。
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,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。
至此,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。
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,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“大屠杀历史”的长段剧情中,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、暴虐、狡诈、伪装。
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,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,通过这样一个转场,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。
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,通过约翰·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。
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,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,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。
历史,不容否认,不容诋毁。
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。
大银幕上,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。
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,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。
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,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。
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:“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。”
“那天中午,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,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。”
“我母亲姓聂,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,顾不得管我们,躲到了桌子底下。”
“日苯兵把她拖出来,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。”
“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,外祖父聂佐成、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,被日军枪杀。”
“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,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。。。”
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,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。
即便已经在法庭、记者、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,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大银幕上的刘伊妃,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,同时泪崩。
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,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,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。
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。
镜头推进,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