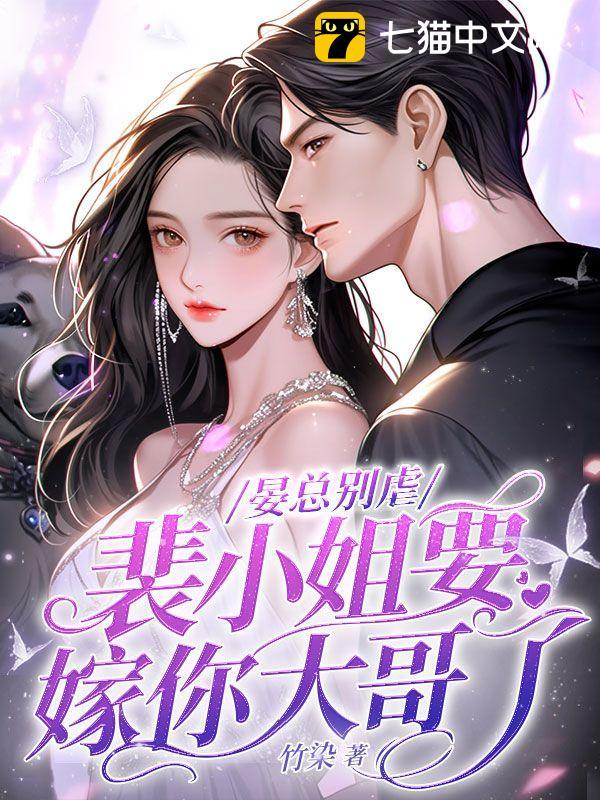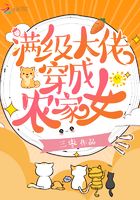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黛玉清穿文 > 14第 14 章(第2页)
14第 14 章(第2页)
恪敏走得更快了,将人甩在身后,跑回了院子。
保绶停步想了一会儿,叫人去打听。
不过片刻,便有人就来回话,“是巡盐御史林海府上的大姑娘。”
保绶听了,喜得一拍掌,“哎呀,林如海?那不是好事么?”
说着要赶去恪敏院中,转念一想,又命人备马,匆匆出门去了。
恪敏板着脸回到房中,还当今日会像往常一般,引来一顿说教,谁知等了半日,也不见二哥跟来。
命人去打听,却听说保绶又匆匆出门去了。
恪敏不由暗骂一声,“蠢才!定是又进宫去找太子献殷勤了,他怎么就不听劝?上头的人可还在呢,就冲下任使劲去了……早晚有一日,受到报应!”
还有句更加僭越的话,她藏在心里不敢说出口——上头的那个是主子爷,这是万民皆知的,而毓庆宫的那个,现在看着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,将来何去何从谁能说得准?
她一个闺阁女子,见不到主子爷如何宠爱那位,可她会看戏,古往今来,太子成功继位的不过五五开。裕亲王府是皇族近支,便是不急着捧太子的臭脚,一时半会儿也倒不了。
畅春园佩文斋中,康熙皇帝正坐在御案后批阅奏折,屋子中四处静立着太监,却鸦雀无声,有那些进出奉茶添香的,也都弓着身子,一点儿呼吸声也闻不见。
这时,李德全从外头蹑手蹑脚地走进来,弓着腰,抬眼撇了下康熙,立即又垂下,低声道,“皇上,四阿哥在外头求见呢。”
过了片刻,康熙写完最后一个字,搁下笔,伸展了下腰背,喉间溢出放松的呻吟,下意识透过纱窗望着外头的天色,“叫他进来。”
“是。”
胤禛弓着身子进来时,康熙将方才批过的折子合上,随手放在已摞了不少的一沓折子上头。
他手上捧着个匣子,进来便放在一旁,打了打马蹄袖,跪下扣头,不敢乱瞟。
康熙叫了起,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捧进来的匣子,搓着手道,“老四,少见啊,你带这匣子来,有什么说道?”
胤禛这才敢抬头,上、首的康熙戴着绒草面藤竹丝胎青绒便帽,帽檐镶着一粒黄豆大小的东珠,剪裁得体的石青江绸暗团龙纹常服袍,领口微露云纹缎边,腰间系着明黄涤织金纽带,悬白玉佩、火镰袋、槟榔荷包。
这时稀奇地走了出来,“起吧,这里头装着什么,给朕瞧瞧。”
胤禛谢了恩,捧着匣子放到旁边的高几上,笑着打开,“这东西,是偶然得来的,皇上瞧瞧喜不喜欢。”
康熙定眼一瞧,只见匣子中放着块平板琉璃,角上似还有些杂质,四周用雕花木框包了起来,蹙眉拿在手中,上下左右瞧了个遍,“这琉璃有何稀奇的?即便你把它做成这古怪的模样,它也还是琉璃,变不成金子!”
胤禛笑道,“皇上听儿子说,这琉璃是用新方子做的,取材十分廉价,比以往的旧方子成本降了七成。”
康熙点头,若有所思,“那做成这平板的一块,又是为了什么?”
胤禛道,“此乃下头人给的意见,若将琉璃覆于书画上装裱,能将其更好地保护起来,又或者,作为糊窗之物,比起纱窗、纸窗来,更加保暖透光。”
康熙下意识看向窗上的高丽纸,这是一种用棉茧或桑皮制造的白色棉纸,透明白净且质地坚韧。他将平板玻璃举在一旁对照,“是比纸要亮堂!且不惧风雨。”
胤禛察言观色,知晓康熙心情大好,趁热打铁道,“皇上,这种制作平板琉璃的法子也是随新造琉璃方一同记载的,价格低廉,原材易得,普及到民间并无压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