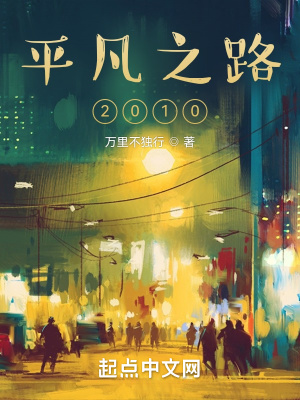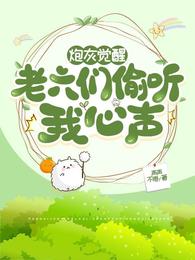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我全家都穿到古代了 > 第138章 募捐(第1页)
第138章 募捐(第1页)
“是呀,我们家前些日子也捐了好些米粮给了寺里,过些日子也是打算设一个粥篷的,不用特地再募捐吧?”
旁人也跟着附和,或说自家已捐过钱,捐过粮,又或说仆从多、口粮难匀。
柳闻莺见陶大娘子的脸上的笑意未减,眼底却掠过丝淡凉——似乎对方早料到会有这般说辞。
只见她又抬手压了压,待场面静了,才缓缓道:
“各位有善举,是该赞的。只是各家单打独斗,粥棚散在各处,有的百姓跑断腿也未必能喝上一口。
若是咱们凑在一处,定个章程轮流照看,今日你家出粮、明日我家派人,既省了力,也能让更多人得济,岂不是比各自为战更实在?”
“知府夫人说的是。”
让柳闻莺惊讶的是大太太蒋氏率先开了口,二太太在一旁也没有露出任何惊讶或者不同意的表情。
瞧着,应当是先前通了气的。
是了,她们家老爷和知府大人可是一块共事的,如今知府夫人宴席上弄这些,若是心血来潮那绝对不可能,精心准备那人群中就该有自己人为其发声。
蒋氏就算再看不上陶大娘子,关键时候也不会给苏照掉链子。
见到有人应和,其他的一些夫人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应了起来。
不过陶大娘子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这么一点,见大家已经开始默认了刚才的事之后,陶大娘子便继续开口,这次的语气里添了几分郑重:
“再者,昨日听夫君说,北地四州同气连枝,尤其是与咱们挨着的燕州与咱们钦州更是唇亡齿寒。
因为旱情和粮草调度问题,燕州大营的将士们如今每日只能喝稀粥度日。如今百姓要救,将士们的生死更是不能不管。”
陶大娘子说起这话的时候,苏媛的身子立刻绷紧了起来。
陶大娘子起身朝众人略一欠身,目光真诚,言辞恳切,说道:“施粥是为百姓积德,捐粮给军营,却是为咱们家国守着底气。
各位姐妹家里都是受朝廷恩典的,若是能做个表率,既让百姓念着咱们的好,也让将士们更好的应对今年胡人的秋袭,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事,你们说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