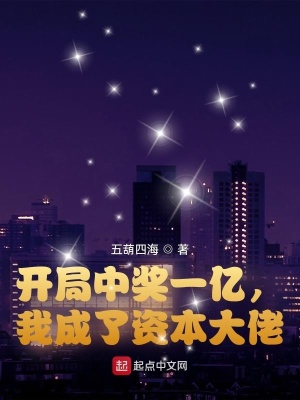爱尚小说网>武田幕府名将 > 第三九三章 石山本愿寺的重要性(第3页)
第三九三章 石山本愿寺的重要性(第3页)
因此,织田信长想要的,就是本愿寺所在的大坂这块地,以及支撑本愿寺寺内町的生产力和运输能力。
如此看来,织田信长出的“难题”,就是要让本愿寺御坊从石山搬出去。
本愿寺起兵之后的九月二十九日,曾在本愿寺暂住且起兵的时候可能就在寺内町的前关白近卫前久,给显如写了封信,在信中说本愿寺的起兵是无谋之举。对此,显如回信说:信长肆意妄为,本愿寺实难忍受。(《显如上人文案》)
换言之,信长出的“难题”,对于本愿寺而言实在是无法忍受之事。即便如此,信长还是威胁说,如果不答应自己的要求,就会大肆破坏。
这里说的破坏,与其说是针对包括寺内町在内的石山本愿寺全境,不如说是破坏本愿寺的御坊。
过去,信长在进攻美浓斋藤氏的时候,是在对斋藤道三所设立的加纳自由贸易市场加以保护的前提之下,对稻叶山城的斋藤龙兴发起进攻,并把他驱逐出去的。
再者,在使木曾川沿岸交通要地上的富田圣德寺屈服的时候,信长也答应保护寺内町,这才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。
顺便说,这个圣德寺就是织田信长和斋藤道三曾经会面的那个寺院。
《信长公记》卷首记载:这个叫富田的地方,是个有七百户民家的富贵之处。大坂(石山本愿寺)向这里派遣“代理坊主”,这里还持有美浓、尾张的守护所颁发的“判形”(税赋杂役免除文书),享有特权。
可见,这里也从领主那里得到了“寺内特权”,愈发繁荣起来。
由此可以想见,织田信长意图通过让本愿寺御坊从大坂搬出去,获取对寺内町的控制权,进而掌握具有贸易实力的大坂全境。
如果不把本愿寺从大坂搬出去的话,就毁坏御坊。织田信长所出的“难题”就是这个吧。然而,面对这样的要求,本愿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。
石山本愿寺是第八代宗主莲如开创的,这一点自不必说,自京都山科的本愿寺毁于兵火以来,历时四十年,此地已经成为凭本愿寺自己的实力构筑的佛法之城。失去石山,不仅是背弃莲如的遗训,还可能使宗主亲鸾圣人的法脉自此断绝。
在显如给近江中郡信徒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话:为保开山祖师所创的门派不遭灭顶之灾,望各位不惜性命,恪尽忠诚……
离开此地就会导致门派断绝,从这句话中,可以看出本愿寺的危机感。信长出的“难题”,被他们视为对本愿寺和本愿寺信仰之存续的否定。
信长之所以坚持要本愿寺撤出石山,主要来讲有两大战略意义。
首先第一点,让本愿寺屈服,从大坂退出去,可以弱化那些还与各地大名勾结的本愿寺信徒的势力。特别是支持三好三人众的阿波、赞岐的信徒,以及与浅井长政、六角承祯协作的近江信徒。一般认为,他们的背后有本愿寺的指示。
因此若能击败本愿寺,那么本愿寺将失去凝聚力,各地的信徒势力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,一定会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。
信长已经将尾张信徒的中心富田圣德寺据为己有,此外,连接美浓和京都之间的道路上的大津通往京都入口处的近松显证寺、京都大坂往返必经之地的淀川流域的摄津高槻富田教行寺,还有河内招提的敬应寺、枚方的顺兴寺、八尾久宝寺的显证寺,这些寺内町都已屈服于信长。信长向他们下发朱印状,保证他们的安定。
这些寺院、道场并未受到破坏,信长是在保证寺院和寺内町存续的基础之上,对其实施控制的。
这样想来,如果本愿寺也服从信长,本愿寺和寺内町的存续也能得到信长的保障。面对统率各地信徒的本愿寺,信长唯独对大坂之地的存续不予认可。
这其实是织田军“武家”统辖天下的逻辑与大坂的信徒、百姓同心自治的中世式的逻辑之间的矛盾。藤木久志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,即织田信长的目标是对后者的完全掌控(《统一政权的成立》,岩波讲座《日本历史》第九卷)。
另外,信长的战略目标的第二点,前面已经提到,就是看中了石山本愿寺所在的大坂的地利。
十年后本愿寺从这里撤出,织田信长以此为城郭,将这里作为进攻毛利氏和四国长宗我部氏的据点。我们知道在信长死后,羽柴秀吉也在这里筑城。这里是面朝大坂湾的上町台地最高处的尖端部分,地理条件非常优越。
而且这里还邻近淀川、大和川等河流的入海口,可以作为港口使用。这里已经作为繁荣贸易港堺和兵库之间的新兴贸易港,引起了世人的瞩目。